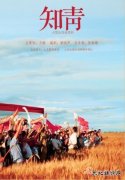光影里的军魂,岁月中的敬仰
|
小时候的夏夜总裹着热气,晚饭的油烟还在檐下打转,我已攥着小板凳扎在黑白电视机前。屏幕里跳动的光斑像暗夜里撒下的星子,而战斗片里的枪林弹雨,总让我心潮翻涌。《地雷战》《地道战》《小兵张嘎》《平原游击队》——这些在光影里滚动的名字,早就在我稚嫩的心上,刻下了对军人的滚烫崇敬。 看《地雷战》时,眼睛总瞪得像铜铃。那些埋在田埂下、墙角边的“土家伙”太神了:陶罐里塞着炸药,石头缝藏着机关,连废弃的铁犁都能改造成让敌人胆寒的“铁西瓜”。当侵略者的皮靴踩响引线,炸开的烟尘里混着村民们憋红了脸的笑,我总攥着衣角在电视机前蹦跳。记得有个镜头:白发苍苍的大爷蹲在菜窖里削木雷,皱纹里嵌着泥灰,指尖磨出的茧子蹭过木雷边缘,眼神却亮得像星:“这土地是咱的,鬼子休想踏进来!”那一刻突然懂了,军人的勇敢从不是蛮勇,是把绝境织成坚韧的网,是把苦难嚼碎了咽下的智慧。 《地道战》藏着另一种震撼。村口老槐树洞里藏着入口,灶台底下连着通道,连水井壁上都凿着暗门——那些在地下蜿蜒的 “长龙”,是村民们用锄头、铁钎一凿一刨抠出来的。敌人端着枪闯进空荡的村庄时,哪知道脚底下正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他们;当冷枪从菜窖里、墙缝里钻出来,他们才惊觉这片土地早变成咬人的钢牙。影片里那个年轻媳妇,背着孩子在地道里传递情报,布鞋磨穿了底,奶水浸湿地襟,却始终把“小心地雷”的暗号喊得清亮。这画面比任何冲锋陷阵都让我鼻酸:军魂不止在军装里,更在每一个愿为家国挺身而出的普通人骨血里。 《小兵张嘎》里的嘎子,是我刻在铅笔盒上的英雄。他歪戴草帽,裤腿卷到膝盖,手里的木头枪比真枪还攥得紧。为了给被鬼子杀害的奶奶报仇,这个本该在田埂上追蝴蝶的孩子,把恐惧嚼碎了咽进肚里,跟着游击队摸岗楼、送情报。记得他被汉奸抓住时,明明吓得浑身发抖,却梗着脖子骂“狗汉奸”;记得他得到真枪时,半夜在草堆里摸来摸去,嘴角的笑能甜到梦里。嘎子让我明白,英雄从不是天生的“超人”,是哪怕怕得想哭,也会咬着牙往前冲的普通人——就像邻家哥哥,就像巷口大叔,只是在危难时,把“怕”字换成了“敢”字。 《平原游击队》总带着股烈劲儿。李向阳骑着马在青纱帐里穿梭,马靴踏过庄稼地的声响,比雷声还让人振奋。他带的队伍像地里的蚂蚱,一会儿钻进高粱地,一会儿跳进芦苇荡,把装备精良的敌人耍得团团转。最难忘那场夜袭:队员们借着月光摸进炮楼,匕首划破夜空的轻响比枪声更惊心动魄,当“缴枪不杀” 的吼声撞在炮楼砖墙上,我攥紧的拳头里全是汗。原来军人的 “勇”,不止是敢死,更是敢活着跟敌人周旋到底,敢用千般计策护一方百姓周全。 时光把黑白电视换成了彩色屏幕,我也从孩子长成了大人。刚参加工作那年,单位老会议室的幕布上放《三大战役》,昏暗光线下,几百人的呼吸都轻得像羽毛。辽沈战役的冰天雪地里,战士们趴在雪窝里啃冻土豆,枪栓冻住了就用体温焐;淮海战役的战壕里,伤员咬着木棍包扎伤口,血把黄土染成褐红;平津战役的城墙下,冲锋号响起时,无数身影迎着炮火往上冲,像潮水漫过礁石。那些宏大的战争场面里,我突然看清“军人”两个字的分量:不是电影里的酷炫镜头,是冻裂的脚掌、带血的绷带,是明知前面是死路,还愿意把后背留给战友的信任。 后来在新闻里看到,持续强降雨让北京延庆、怀柔、密云多处受灾,武警部队紧急奔赴现场救援:他们蹚着齐腰深的洪水转移群众,用身体搭成人墙挡住滑坡的泥土,在齐膝的泥浆里扛着老人往安全地带走。那些泡得发白的脚、磨破的手掌、嘶哑的呼喊,突然让我想起老电影里的画面——原来那些光影里的军魂,从来没离开过。他们换了军装的颜色,换了战斗的战场,却始终揣着一颗“为了谁”的心:为了田埂上奔跑的孩子,为了窗台上盛开的花,为了我们能坐在灯光下,把日子过成诗。 如今每次经过军营,听到整齐的脚步声总会驻足;每次看阅兵式,望见那些挺拔的身影总会眼眶发热。光影会褪色,岁月会流淌,但军魂像天上的星,永远亮在那里。它教会我:平凡日子里的坚守也是英雄气,普通人的担当也是报国心。 这光影里的军魂,是刻在民族骨头上的印记;这岁月中的敬仰,是融进血脉里的力量——从未褪色,永远滚烫。向所有把黑暗挡在身后的人致敬——他们让我们懂得,和平从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,是有人用青春、热血甚至生命,一砖一瓦砌起来的家园。 本网通讯员:石启平 (编辑:东北亚) |

 芦岭矿关工委举办“薪
芦岭矿关工委举办“薪 铁血铸军魂 丹心永向
铁血铸军魂 丹心永向 密营深处寻初心: 从
密营深处寻初心: 从